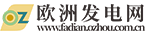
“这颗犹豫的心的跳动”
“This Beating of a Hesitant Heart”
《关于遗忘和希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ON FORGETTING AND HOPE
作者:Joseph D. Kuzma
译者:鼹鼠的死刑判决
(等待心灵的是与他人相遇的前景,在这种相遇中,所有的地位,以及所有的距离,都将被取消,但只是为了使这种随之而来的亲密关系无法在主宰或占有的名义下被概念化。 正如莱斯利-希尔(Leslie Hill)正确地建议的那样,这种相遇的逻辑始终是 "先拆解后表达 "的。 "换句话说,它涉及到 "分离、不完整和不可能的满足,作为相遇的无根据的基础。 "但是,一颗已经破碎的心怎么可能渴望以这种方式破碎了它的相遇的永恒重现呢?当未来本身允许那毁灭性的打击返回时,心如何能肯定地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毫无疑问,这是在布朗肖阅读尼采之后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它似乎表达了一种恐惧,一种犹豫,一种理解,这种理解远远超出了思辨哲学或批判理论的范畴。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为了接近生活和爱的真正意义。因为谁没有感受过爱情毁灭性打击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呢?谁没有从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中走出来呢?然而,正是这种相遇,曾经使我们颠沛流离,将来还会使我们永远颠沛流离。正是这种相遇每时每刻都在拉近我们,拉近被它撕裂的人。鉴于这一切,心如何能坚持肯定一个未来,它的淫荡承诺,但不断复发的创伤,重新开始?心怎么能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破碎呢?
从尼采到布朗肖,答案都是一样的:只有通过遗忘。只有遗忘才有能力见证“打破历史”、使人心碎的迁移。仅仅是遗忘,让我们“思考这个断裂”,让我们远离自己。这是布朗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不断重申的观点,与永恒回归的思想有关。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只有在遗忘的模式下,尼采才有能力思考这种令人神往的思想。 只有遗忘才能够 “将未来从时间本身中解放出来”--将它从任何决定性的恢复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
考虑到这一切,发现布朗肖在他1954年的特里斯坦论文中,首先强调遗忘的概念及其与情爱的关系,是不是很吸引人?“也许我们必须抓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故事背后的阴影,”布朗肖写道,“遗忘是一个沉默而封闭的空间,欲望在那里无休止地徘徊;当一个人被遗忘时,他/她是被渴望的,但这种遗忘必须是深刻的遗忘。”布朗肖的意思是,渴望对方,渴望能让她靠近的相遇,就必然会忘记她。换句话说,这正是一颗伤痕累累的、破碎的心如何能够走向未来的方式。是渴望她再来,总是再来,但只是披着遗忘的外衣,总是不认识她,不认识她。这一概念布朗肖1962年的作品《等待遗忘》(waiting Oblivion)中得到了简洁的阐述,我们在书中发现了如下的交流:
-“你会忘记我吗?”
-“是的,我会的。”
"你怎么能肯定你已经把我忘了呢? "
-“等我想起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我会确定的。”
如果破碎的心,在他的叙述中,发现自己不断地等待着伤口的重新愈合,伤口在每一个开始之前就已经标记了它,那么这种等待也必须被理解为与“深刻的遗忘”不可分割。只有遗忘,才允许对这次相遇的无条件肯定发生。《等待遗忘》的主人公意识到,只有遗忘“才能让我们团聚”。
从这些方面理解,人们甚至可以说,忘记亲密,恰恰是记住它。忘记心碎的痛苦,是最接近再次经历心碎的痛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布朗肖在他的《无尽的谈话》的后期补充内容中所写的那样,Lethe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亲密的“爱神的伴侣”。我等待着,一直在忘记——这样,亲密的相遇就能再一次,永远地回来。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本中,布朗肖明显忽视了任何关于亲密关系的实质性讨论,他几乎完全避免了亲密关系的修辞,这是否表明了一种更深刻的准备接受亲密关系的行为——就像克尔凯郭尔的话语中的约伯一样,等待着重复?那么,这一切是否进一步表明,在布朗肖的叙述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顽固的希望?
希望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最后,让我简单地说一下,如果在布朗肖的情色描述中还有一丝挥之不去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必须被理解为根本无法简化为任何可以一劳永逸地实现的完美幻想,就像它无法简化为任何可以最终得到满足的渴望一样。在1959年一篇关于诗人伊夫·邦尼福伊的文章中,布朗肖沿着这些思路告诉我们,“希望将被重塑”的概念——换句话说,它需要从对绝对和解或绝对知识的向往中解脱出来。“与理想擦肩而过的希望,”布朗肖写道,“是微弱的希望。这是因为,任何与“理想状态”概念相联系的希望,都不能不暴露出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明显厌恶,一种对意外的厌恶。亲密和知识、爱和认可之间的联系必须被打破。
布朗肖准备提出什么替代方案?在1959年的一系列评论中,他继续告诉我们,当希望区别于(并剥夺了)“所有明显的希望”时,希望变得“最深刻”。换句话说,当它把自己与最不可能、最不可能、最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时,它就变得最深刻。如果在布朗乔式的情爱场景中仍有一丝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就保证我能永远重复,而且完全不可预测地重复最美丽、最偶然的时刻——但前提是我总是被排除在这种希望之外。这种希望给我的承诺,无非是我所爱的人自己的回归——但只是以一种闪烁的形象的形式,在蒙帕纳斯的夜晚,一个转瞬即逝的剪影——总是在一个巨大的、相互穿透的光场的非人性的幽灵中消散。
谈论布朗肖式的希望,就是谈论亚伯拉罕的希望,一个人的沉默的希望,他起得既不早也不晚,而是在精确的指定时间登上山峰,以便进入一种最可怕的、不可证实的相遇,使他与一个形象保持亲密的状态。这就是布朗肖式情爱场景的希望:情人的脆弱的希望,他甚至肯定了最深的隔阂,最绝对的距离,没有任何回报的愿望——知道只有通过令人着迷的撕裂的时间和推翻所有的存在,他也许可以通过客观的想象的光芒,回到他所爱的人身边。
想想《不逾之步》(the Step/Not Beyond)的最后几句话。布朗肖写道:“他在临终时是如此平静,以至于在临死之前,他似乎已经死了;之后,永远,仍然活着,在这平静的生活中,我们的心为之跳动——这样就在那一刻抹去了极限,而它正是在那一刻抹去的。”这些话想要表达的是人心的极度不稳定。在被彻底分裂之后,它在持续不断的暮色中徘徊,这是一次最不可能的遭遇的后果:与他者的遭遇,与死亡本身的遭遇。这是一次让它破碎的相遇,但仍然肯定地与未来有关。这一关系在以下文字中被引用,文本的结论是:“在即将到来的夜晚,让那些已经团结起来的人,让那些互相抹杀的人,不要把这种抹杀视为他们将对彼此造成的伤害。”
如果布朗肖选择用这些话来结束他的文本,那么它既没有向他的读者发出任何最终解决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终极真理的暗示。更确切地说,这些话所包含的是一种温柔的劝告,一种微妙的安慰,对那颗等待着那一刻的心来说,那一刻总是使它破碎,而且还会再次使它破碎。当夜幕降临,它将永远赦免我们,布朗肖坚持认为,这种破裂将不会是我或我自己造成的伤口。这是因为我永远不会在那里;你也不会。当一颗心破碎,当它因爱而破碎成碎片时,这一刻撕裂时间的暴力本身只会表明一种非个人的、无名的崩溃。就像永恒回归的想法会让那些想要思考它的人望而却步一样,一种伤人的亲密关系的出现也会让我免于经历它。因此,布朗肖建议,让我们以一颗平静的心等待它,甚至肯定这一幕没有证人,肯定这一事件没有参与者,肯定这一动作没有深度。这就是《不逾之步》最后得出的证词。这是一种见证,它不寻求恢复尼采的永恒回归的愿景,但成功地将思想的思想带到了众所周知的极限。
如果时间无情的循环占了上风,那么所有这一切只是漫长的序言的开始,它将引导我回到那个地方,在那迷人的平静的一瞬间,我们都消失了
选自The Eroticization of Distance Nietzsche, Blanchot, and the Legacy of Courtly Love